
彎彎曲曲的小路,兩旁挺拔參天的樹木,田間一般時節都是郁青地水蹈,農閒時改栽油菜花,使一路景緻增色不少、耀眼無比。明杏黃澄的茫茫花海中滲透一股石英礦味,那是山間坑道的勞動成果,代表著富庶、隱喻著生機,暗示家鄉土地多麼無私地養育人民。這雖是返家的路,卻也是離家的路,離別總是那麼的快且突然,同樣的距離硬生生被機械式地反轉,轉到誰也意料不到的劇情之中。
這段劇情,來得莫名、來得突然,似乎大幕還沒有揭開、燈光尚未定位,便糊塗開始。也無人知道,這段劇情的大幕,何時落下。
那是灰蒙蒙的一群人,甫退至瓊島還沒來得及歇腳,大隊又往古寧頭,喊打喊殺。戰爭嘛,過去幾十年也夠多了,打外人、打自己人,打贏了沒好處,打輸了提早輪迴,搞不好下輩子還得繼續打……管不了那麼多,戰事稍息,他們列隊排好、一一登艦,這不是旅行,而是命令,奉命前往陌生不可測的東南島嶼。
甲板上站滿了人,卻不喧鬧,失去所有生氣,艦身本來灰色的塗裝本就顯得冰冷,轟鳴的輪機噪音曳引著大鐵殼緩步移動,在茫茫大海中,多麼孤立無助。軍人們難以制式著裝,皆是不甚合身、破損污穢的灰粗麻料、綁腿及配有藍徽的軍帽用以遮體,連同多人臉上,沾上黑黑髒髒污垢,唯一鮮豔的,恐怕只有包紮用的白紗,及滲透出來的紅汁濃血,怪不得後世有政治狂熱者,斷定這一批人「軍容不整,使島內民眾大失所望」。
也許他們自感慚愧,深知這樣的軍容儀表難見海東父老,可又有什麼積極正面的手段可以挽回這一切呢?現在,只有在這艘大鐵殼上,望著洶湧的黑水溝,淘淘浪花注入早已空洞呆滯的思緒中。
歷經那麼多年,一路走來莫名其妙:家鄉出暴動,縣城徵兵組織保安隊,為讓家中胞弟能讀書,只好去了;日本軍閥殺同胞傾略土地,因政府強力號召全面抗戰也只好原隊轉移,只好去了;後來爆發內戰,場場大役一移轉就是數百萬人,於是跟隨原編制成為掌權者的棋子,只好去了……初衷呢?是為家鄉安定嗎?為家人順遂嗎?那太遙遠,打從十六歲離家起,那些早已是幻影,「家鄉」這一概念,就如同四處爭戰時上面頭兒們所宣揚的一切,空的,虛的,沒有意義。
聽說艦艏前方是一座美麗之島,但曾發生過治安慘案,民心不穩,天災甚多,是否預告接下來仍不順利?藍藍的海水伴隨著白浪,如同古老巫術驅邪儀式一樣掃除艦上官兵的滿身塵埃,在艦艏前方日光灑下處,已可看到一小塊翠綠如玉似的地面展現揚姿,像離家時老母親為他們配戴的家傳首飾,雖然只是隱隱約約,但對於這群失去家鄉關愛的人們,最渴望踏上一塊紮實飽滿富含營養的土地啊!只有大鐵殼感受不到這份溫暖,緩慢踏浪,給予艦上全體將士還算充裕的時間,對未來描繪藍圖、略施想像。
有人想嚐島上的青菜水果;有人想討個媳婦;有人想繁衍香火;有人希望找個安身立命之所;有人只求神明保祐健康;有人想著怎麼應付島上的不穩定局勢;有人只想休息一陣子,再隨部隊回大陸,最好能回家……
很多人,想家。想啊、想啊、想……,真正想起一件重要的事,就是到底有多少年沒能好好地「想」?對於這群灰色人類而言,「想」是一種奢侈。只有大鐵殼這艘不會亂想的物體,堅定不移地恪守信念地冷靜地理性地……往基隆港開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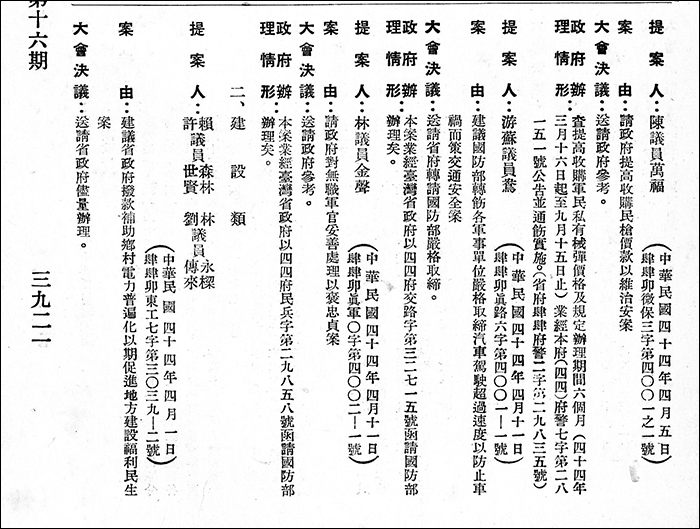
又開了很久,也暗暗想了很久,翠玉越來越大,那就不是翠玉了,是一坨藏青色也帶點鐵灰的布料,像久未清掃的縣城劇院,那尚未開啟、不知藏有什麼二流劇碼的大幕。這群軍人沒有什麼行李好收拾的,把柺杖拎好,將想了很久的思緒整理好,準備聽從下一個號令指揮。
轟轟轟,大鐵殼減速了……轟轟轟,微微地調整方向……轟轟轟,緩緩向碼頭靠齊……
突噜噜噜……宕!
一艘滿員軍艦完成了它的階段使命,將這些與自己同色的人群載往目的地,當發出巨響靠向碼頭時,所有人的心裡也如大鐵殼一樣暫時鬆懈,想著至少可以獲得短暫的平安。
有人鼓起勇氣,略帶期望的眼神餘光,偷偷地、小心地從船艙瞄向岸邊,嚇然發覺,那碼頭上迎接自己的,不是彩花、橫幅、鞭炮、美女,而是一隻隻曾經用來打外敵的步槍、火炮,都是武器、武器、武器。大家發現,自己被盯上了,原因呢?與過去幾十年發生的諸多事情一樣,未明。
一名高階軍官,帶著若干持槍護衛,登入艦身。高官的大盤帽顯得很張揚,戴著白手套表現一種貴氣,又因為大鐵殼龍蛇雜處,通風不良,高官掏一白帕捂鼻,排斥那令人作噁的髒空氣。約一小時,高官及幾名護衛出艦,可多了一人,步伐沉重、垂頭喪氣,正是這整船灰色軍人的最高長官,人稱「柏公」,原也是軍機要員,可在山頭各立的年代,能少一公是一公……
碼頭上停滿了軍用大卡車,出現幾名少校把全艦人員引下,依「官」、「兵」分類,就像垃圾分類,軍銜低的兵,排列整齊,二路縱隊:齊步──走!沒有廢話,全送上卡車,一輛輛駛出基隆港,早已轉進來臺的各軍大將等著增配額度,壯大門派。
碼頭上,負責管制、引導的軍官們,確認現場利益全部榨乾抹光之後,迅速離場,和之前兵敗如山倒一樣地快。自船上走下,本已落魄不堪的尉、校軍官,在空蕩的碼頭邊,吸收著雨都的溼氣,無人招呼聞問,其手足無措、驚訝無神之感,有如甫從家鄉離開、編入軍隊、殺人打仗、登船而走,只是從大陸轉變成海洋,又轉變成一處人生地不熟的小島雨港,持續恍惚。
基隆多雨,潮濕的氣候更加深灰色的無奈,這群人沒地方住、沒食物吃,只能在港邊流浪、流浪、流浪。半世紀後,有心人嘲諷當年來臺軍人紀律不整,但誰都相信紀律不可能凌駕在衣足飯飽、人格尊嚴之上,那已經不是為了生活,而是妄圖生存。
初來乍到,語言不通、習俗不適,本省人嚇著不敢靠近,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外省人擔心這樣下去則橫屍街頭客死異鄉,雖然「客死異鄉」對他們而言已是過去幾年很可能發生的事,但他們沒想到,最終令他們這麼難堪的,是戴著同樣帽徽的同一陣營。
像百浬外的浪花滾上了岸,一股情緒總算按耐不住,有人偷食物,搶奪任何能維持生命的物品,使城中混亂的治安情勢,像光亮火柴不慎掉入艙底燃油,猛然燒開、愈燃愈烈……當局見狀,為避免幾年前暴亂事件重演,果斷壓制,將這群失去組織的軍官集合起來,豢養幾天,貪一時穩定。也不知哪位絕頂天才獻策,為求長治久安,將這群被惡意遺扔丟棄的人群,編入一個特殊組織──
「無職軍官團」。
這麼矛盾離奇的文法,正是他們接下來的正式身分。「無職軍官」,從某種程度上,這些人仍被認定是堂堂國民革命軍的軍官,但因情況特殊、人力需求驟減,所以不能給他們任何職務。其實,若軍源過剩,大可裁員,但當局總是怕民心不穩,若把這些人徹底解職,要是叛逃該怎麼辦?寧可緊箍一百,也不鬆懈一個,透過這另類的軟性綁架手段,總算政權茍延殘喘。
又來了幾輛依舊是低沉厚實的卡車,就像當時駛往碼頭分兵的那樣,把這群無職軍官們一一歸類,送上車、開走。有的開往宜蘭、花蓮,有的開往臺東,有的前進梨山天冷,有的駛入苗栗獅潭山區,他們沒有先進的工具,也沒有專業技術,憑藉著一身臭皮囊及幾副簡陋至極的金屬器具,開路、拓荒、闢農場、蓋地堡壘。有的總算因工程意外能「客死異鄉」,有的則是乾脆在道路終點處,落地生根,趁局勢混亂模糊間,趕緊辦理退伍,覓一小屋弄點買賣,成家立業。
萬幸,開路鑿山的終點,是棲身之所,雖不見廣懋的油菜花海,但四周的硫磺坑與山林、彎彎曲曲的小路、不算太擁擠的環境、閑靜的村庄……,倒是與模糊的原鄉有幾分神似。
算了,暫時就把這兒當家吧!至少,再也不要過著沒有明度、毫無色調的日子,至少可以從這塊複刻境地上慢慢拾回自己,逐漸把生命的顏料填滿,直至亮麗如油菜放耀光明。日子過得清貧困苦,卻能讓頭腦開始運轉,就像當時那艘軍艦有力的引擎,把心思運載到不知多少公里外的故土,穿梭在現實與夢境間。這一想,還真想開了,甩開虛名、掙脫一頂紙帽子。
能夠掙脫紙帽子的還是少數。大多無職軍官只能聽從號令,繼續被束縛著,大約維持三、五十或更多歲月,為一個虛幻的政權信仰奉獻己力,即使,他們已經無職。
